第三人主張權利什么意思_第三人主張權利什么意思?
 特邀律師
特邀律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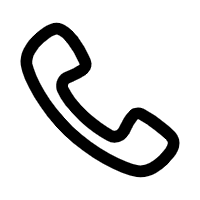 咨詢不收費,免費提供專屬維權方案!
咨詢不收費,免費提供專屬維權方案!
當合同雙方當事人的行為侵犯第三人權利時,第三人有權行使相關權利以維護自身的利益
以下說法正確的是 B執行可能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且中止執行不損害公共利益的,中止執行 D行政機關不得對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電、供熱、供燃氣等方式迫使當事人履行相關行政決定 第三十九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中止執行: (一)當事人履行行政決定確有困難或者暫無履行能力的; (二)第三人對執行標的主張權利,確有理由的; (三)執行可能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且中止執行不損害公共利益的; (四)行政機關認為需要中止執行的其他情形。 中止執行的情形消失后,行政機關應當恢復執行。對沒有明顯社會危害,當事人確無能力履行,中止執行滿三年未恢復執行的,行政機關不再執行。 第四十二條 實施行政強制執行,行政機關可以在不損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權益的情況下,與當事人達成執行協議。執行協議可以約定分階段履行;當事人采取補救措施的,可以減免加處的罰款或者滯納金。 執行協議應當履行。當事人不履行執行協議的,行政機關應當恢復強制執行。 第四十三條 行政機關不得在夜間或者法定節假日實施行政強制執行。但是,情況緊急的除外。 行政機關不得對居民生活采取停止供水、供電、供熱、供燃氣等方式迫使當事人履行相關行政決定。
第402條規定的情況 第402條規定的是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知道受托人與委托人之間的代理關系的情況,這時,該合同直接約束委托人和第三人,但有確切證據證明該合同只約束受托人和第三人的除外。該條實際上是《日本民法典》第100條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的翻版。《日本民法典》第99條規定,“代理人于其權限內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直接對本人發生效力。前款規定,準用于第三人對代理人所進行的意思表示。”第100條規定了未明示為本人的行為,“代理人未明示為本人而進行的意思表示,視為為自己所為。但是,相對人已知其為本人所為或可得知其為本人時,準用前條第一款的規定”。〔31〕《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1項規定:某人在其享有的代理權限范圍內以被代理人的名義進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直接為被代理人和對被代理人發生效力。第2項規定:表示是否明示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或依情形表示是否應以被代理人名義進行,并無區別。〔32〕 綜合考慮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并借鑒《日本民法典》、《德國民法典》的上述規定,我們可以分析得出第402條的構成。 首先,受托人是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如果受托人以本人名義訂立合同則直接適用代理的規定,發生代理的效果。 其次,第三人知道委托人與受托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我國有學者認為,第402條的適用前提為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即受托人雖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但不指出委托人究竟是誰。〔33〕還有學者認為,知道委托人與受托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是明確知道,而不包括應當知道,也不包括知道得不確切的情況。知道的內容包括具體的被代理人和委托授權的內容及期限。〔34〕筆者認為,該條適用的前提應該是第三人知道或者應該知道代理的事實以及被代理人是誰,而委托授權的內容以及期限則不必知道。因為如果是出于保護第三人的目的而做這種解釋,就有些杞人憂天了,畢竟還有表見代理制度來保護信賴代理外觀的相對人利益。筆者這樣定義知道的內容主要是基于以下理由。 首先,如果對照《日本民法典》第99條和第100條的規定、《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規定,我們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第三人必須知道本人是誰,否則他也無法將法律行為的后果直接歸屬于本人。日本學者在解釋第100條但書適用的情形時,進行了舉例說明:雖然本人的姓名沒有明確指示出來,但是,從具體情境能夠推斷出本人是誰,例如在某經營場所內雇員進行的行為,一般來說就是為經營者的雇主(本人)所為的。〔35〕其次,如果從體系上考慮,合同法在委托合同中規定的代理情形是區別于行紀的,如果第三人不知道、也無從知道具體的被代理人,則應該適用行紀的規定。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條規定的情況并非針對的是英美法中的隱名代理。隱名本人的代理并非是表明代理關系存在,而不披露本人,前文已述,這是部分顯名本人,也稱作不公開本人姓名的代理。而“隱名代理”是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是指第三人在訂立合同時不知道或不可能知道與他訂立合同的人是在為另外一個人而訂約,而是以為他是在與同他訂約的人進行交易。〔36〕如果合同的第三人不知道和自己正在進行交易的對方事實上只是代理人,就第三人而言,他認為自己完全是在和代理人進行合同交易,則這時的本人(principal)就是隱名的(undisclosed)。〔37〕權威的法律詞典對隱名代理所做的定義也采取這種理解,如“隱名本人指的是代理人隱匿了自己只是在授權范圍內代表另一個人締結合同的事實;由此,在事實披露后,代理人或者本人都可以訴合同的另一方當事人,也都可以被另一方所訴。”〔38〕“隱名代理(undisclosed agency)于代理人不通知第三人代理之情形而進行交易時成立”。“在代理人進行交易之時,另一方當事人并不知曉代理人是為本人而行為的,此時的本人就是隱名本人(undisclosed principal)。”〔39〕包括臺灣學者在內的我國大多數學者將隱名代理定義為代理人姓名的隱去,而代理關系存在之事實當事人均知悉,這是對英美法中隱名代理制度的誤讀。 再次,從時間上看,知道的時間應該是受托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的時候。因為,事后才知道代理人和本人的關系的話,則無法判斷出第三人要與委托人簽訂合同關系的意圖。第三人要與委托人訂立合同的意愿是在合同締結之初存在的,不能在合同履行甚至違約時做出判斷。 又次,必須沒有證據表明合同只約束受托人和第三人。例如,合同雙方在簽訂契約之時特別約定,合同只拘束受托人和第三人。 最后,從法律效果上分析,該條規定的是直接代理,因為其法律后果直接約束委托人與第三人,而不是賦予委托人介入權或者第三人選擇權。 綜上所述,我們得出,我國合同法第402條規定的原型實際上是大陸法系《日本民法典》第100條的但書規定和《德國民法典》第164條第1款第2項的規定,而不是英美法的隱名代理制度。因此,在分析該條規定時,不能依據隱名代理制度設計其構成,在適用該條規定時,也不能參考隱名代理制度來理解。同時,該條的效果也是直接代理的效果,與第403條的規定聯系不大。 第403條規定的情況 如果受托人以自己的名義與第三人訂立合同,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與委托人之間的代理關系,則適用第403條的規定。這是該條適用的前提條件,但如何解釋這個條件卻得大費周章。從字面解釋,不知道“受托人與委托人之間的代理關系”有兩種理解:第一、根本就不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第二、不知道受托人是受何人所托,但是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我國有學者將該條適用的前提定義為“未披露委托人的代理”,指代理人根本不表明自己為他人代理的身份,更不指明委托人。〔40〕筆者贊成此點解釋。但此點解釋存在著很大的障礙。首先如果是這樣,文面索性就規定“第三人不知道代理關系”了事,免得徒生歧義;其次,本條與第402條使用的語言完全一致——“受托人與委托人之間的代理關系”,那解釋上也應該一致——委托人應該是具體特指的那個人。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與委托人之間的代理關系,也就應該解釋為第三人不知道具體的委托人是誰。〔41〕最后,根本的原因還在于,前文已述,合同法的立法過程告訴我們,第402條和第403條的內容曾經是作為對外貿易行紀的內容放在行紀部分里,那么,只能說明,立法本意中這兩條所規定的就是一種需要特殊處理的行紀關系。因為行紀人是專門做行紀業務的,行紀合同中的第三人知道委托關系存在。既然合同法做出這樣的規定主要是為了解決外貿代理的問題,那么,似乎這樣一種解釋——第三人不知道受托人是受誰人之托,但是知道受托人是受人之托——就是必然了。但如果說該條是借鑒英美法的代理制度做出的規定,那么如此解釋就會使我們的《合同法》犯一個原則性錯誤。因為做出這樣的解釋后,該條規定的情形符合英美法上不公開本人姓名的半顯名代理的情況,而在半顯名代理的情況下,第三人的選擇權是不適用的。半顯名代理中的第三人對本人和代理人享有的權利不是或此或彼的,而是累積的(cumulative),直至其權利全部實現。有兩個邏輯支持這一處理原則:首先代理人必須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人們不會希望完全和一個未知的人做交易;其次,半顯名的本人也是合同的當事人,因為通常情況下,與代理人交易的相對人希望合同為之計算的那個人來承擔責任。〔42〕如此分析后,我們自己也嚇了一跳:該條的規定實際上違背了立法者的本意,反而使立法意圖專門解決的外貿代理問題被架空了。無奈之下,我們的分析也只能參考英美法代理制度中隱名代理條件下的委托人的介入權和第三人的選擇權,不得不忽略適用前提問題。但讓我們欣慰的是,英美法代理制度的發展使得隱名代理與半顯名代理的區別越來越小,如下文詳述的隱名代理中,法院已經開始放棄或者修正第三人的選擇權規則,第三人的地位已經趨近于半顯名代理中第三人。這也許可以作為我們忽略規則適用的制度背景的一個借口。 1、委托人的介入權。 受托人因第三人的原因對委托人不履行義務,受托人應當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委托人因此可以介入受托人與第三人之間的合同關系,直接行使受托人對第三人的權利。這里,委托人行使介入權的條件如下: 其一,因為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托人不能向委托人履行義務;如果是受托人的原因,則委托人可以直接向受托人主張權利,而不必涉及第三人。 其二,受托人向委托人披露第三人。這里的披露內容是指受托人向委托人指出具體的第三人。 在委托人不履行義務導致受托人無法向第三人履行義務,以及第三人的原因致使受托人無法向委托人履行義務的情況下,會發生受托人披露第三人或者委托人的問題。這是受托人的義務,但是,如果受托人不愿意披露第三人或委托人,則只能由受托人自己來承擔法律后果。這時,就需要按照純粹的三方當事人,兩個獨立的合同來處理。 其三,委托人行使介入權要受限制。 我國《合同法》規定的限制條件有兩個:第三人與受托人訂立合同時,如果知道委托人就不會訂立合同,則委托人不得行使介入權;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根據學者的解釋,第三人如果知道委托人就不會訂立合同的情況主要有:第三人和受托人在合同中明確規定,禁止他人的介入;第三人純粹是因為信賴受托人個人而與之締結契約,如非常注重受托人的信用、技能、履約能力等;一些必須要由受托人親自履行的合同,委托人也不宜介入;第三人曾經與委托人協商訂約,因懷疑委托人的信用、履約能力等情況而拒絕與其締結合同。〔43〕 美國判例法確定,在下列情況下委托人行使介入權要受到一些限制。 第一、與向代理人履行相比,對本人履行將給第三人帶來更大的負擔,如第三人向本人履行,地理距離上多出一倍。這時,第三人有權要求額外的費用,或者免除其向本人履行的義務。 第二、代理人或者本人惡意隱瞞了代理的事實。 第三、合同要求代理人親自履行,如代理人是著名的風景畫畫家,同時也是藝術家們的經紀人,同意為第三人的農場做畫,但內心里卻想讓另一位畫家來完成。這種情況下,如果代理人沒有事先向第三人言明是要另一位畫家來完成,則必須由其親自完成。 第四、第三人可以向本人主張其對代理人能夠主張的抗辯權。例如,代理人因另一筆交易而欠第三人100元,則第三人就可以向本人主張從履行中抵銷掉這100元。〔44〕在美國代理制度中,第三人在履行完自己對代理人的義務后,對被代理人可以不再承擔責任,其前提是抗辯在第三人知悉本人存在之事實前成立。因為根據美國代理法重述(第2次)第307(1)(a),在相對人知悉本人存在前,隱名代理人都是合同的當事人。〔45〕我國合同法第403條第3款規定,委托人行使受托人對第三人的權利的,第三人可以向委托人主張其對受托人的抗辯,但沒有就該款的適用做出限定。考慮到第三人有可能和受托人同謀惡意侵害委托人的利益,在委托人行使介入權的情況下,第三人對于委托人提出的抗辯,應該以知道或者能夠知道未顯名的委托人之前存在的抗辯理由為限。 2、第三人的選擇權。 受托人因委托人的原因對第三人不履行義務,受托人應當向第三人披露委托人,第三人因此可以選擇受托人或者委托人作為相對人主張其權利,但第三人不得變更選定的相對人。這里的關鍵問題是,在第三人選定相對人以后就不得再變更。也就是說,如果第三人向委托人主張權利后未獲實現,則第三人就無法再向受托人主張合同義務。這是英美法上的一項原則性規定,認為第三人對于代理人的權利和第三人對于本人的權利是沖突的,一旦選擇其一就不能改變主意向另一方起訴。〔46〕不得變更相對人的規定有其制度背景,如果本人已經向代理人支付了價金,但代理人沒有將其付給第三人,本人是否需要向第三人再付款?在英國法中,答案是“他必須這樣做”!〔47〕我國合同法在規定第三人選擇權的同時,又規定了委托人可以對第三人主張自己對受托人的抗辯以及受托人對第三人的抗辯。這樣,如果委托人已經與受托人了結了債務,則委托人就不會再做出第二次給付。我國學者據此認為,我國合同法的規定實際上與所謂純正的英美法不公開本人身份的代理理論背道而馳。〔48〕但是,如何看待本人對于第三人所擔負的責任,這在美國代理制度的發展歷史上是有過反復的。代理法最初并非是一個顯在的法律分支領域,只是后來因為組織性社團的出現,才使得對其研究和討論蓬勃發展起來。19世紀美國關于代理制度的討論并不區分本人的責任和雇主責任,本人所承擔的責任就是雇主-雇員之間關系適用的嚴格責任。正如約瑟夫·斯托里(Joseph Story)論述的那樣,在一般授權(general authority)的情況下,本人要對代理人的行為承擔責任,即使代理人違反了本人所發出的指示。盡管在特別授權(special authority)時情況不同。這種論點被歸結為地位(status-based framework)說。19世紀中葉,斯托里關于一般代理和特別代理的分類受到了批判。當時社會分工進一步發展,企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斯托里時代,代理人與本人之間通常存在著個人關系,而19世紀的公司大爆炸使得雇員的數量越來越多,他們分散在全國各地,使他們有機會和條件超越代理權限范圍。于是,西奧菲勒斯·帕森(Theophilus Parsons)對斯托里的分類進行批判,提出任何人只能受其個人意志形成的代理的拘束。1876年,弗朗西斯·沃頓(Francis Wharton)在其《代理與代理人法釋(Commentary on the Law of Agency and Agents)》一書中,將代理與雇傭(service)進行了區分,認為前者事關業務經營,雇員有自由裁量的權利;而后者是事務性的操作,雇員必須執行具體明確的指令。這樣,19世紀上葉作為獨立自足的代理法分支,在19世紀下半葉便開始消跡于侵權或者合同法領域之中。沃頓還試圖把本人從雇傭關系的嚴格責任中解脫出來,而采用過失標準。也是在這個時代,代理法被司法實踐看作是合同法的分支。但根據嚴格的合同意思理論(the will theory),要求本人對第三人負責、第三人向本人承擔責任存在解釋上的困難,因為和并不知曉其存在的人進行交易,不能說是意思達成了合致。但法院認為,如果讓本人不承受任何負擔就享有利益是不公正的,因此,隱名本人要對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交易負責。〔49〕20世紀初,美國著名學者亞瑟·科賓(Arthur Corbin)關于合同的論述,影響了對隱名本人向第三人承擔責任的基礎的研究。他認為“違約責任不是當事人協議的結果,而是法律的產物”。〔50〕緊在科賓之后,1920年,哈佛大學法學院的沃倫·西維(Warren Seavey)教授提出,隱名本人對于代理人和第三人之間的合同所應該具有的當事人地位,是普通法上的衡平規則,本人所承擔的責任是法律根據具體情形之正義要求設定的義務,與當事人的意志無涉。〔51〕在今天,當受托人接受了委托人的履行后,卻不能向第三人履行時,該如何處理,美國法院的看法事實上仍然不一致。多數說認為,在本人尚未公開時,如果本人和代理人之間對于債權債務的處理出于誠信,本人認為代理人會向第三人履行,則本人可以免責。而少數說認為,隱名本人并不免除清償之責,除非第三人的行為讓本人有理由相信代理人已經進行了償付。多數說的根據在于,本人基于善意向代理人做出的履行并不損害第三人,因為第三人的預期中,代理人是唯一的交易對方,因此他也必須承擔和代理人之間的信用風險。而少數說的論據在于,得到了本人支持的代理人在第三人看來是完全不同的一個獨立的交易者,而且本人有無窮無盡的措施可以保護他自己。不能因為本人倚賴其代理人的誠實而不是他自己的調查就讓第三人受損。〔52〕和美國法院的多數觀點進行比較,我國合同法的規定與其差距并不大,唯一不同的是,我們沒有對有效抗辯做出限定,從主觀上看,本人向代理人履行的行為必須出于誠信和善意;從客觀上看,有效抗辯必須是在第三人選擇之前存在的。在第三人選擇以后,本人要為第三人的利益做出考慮。因此,《荷蘭民法典》做出了如下規定:如果一個代理人以自己的名義進行交易,違反了他對第三人所負的義務,或者如果他已經破產,第三人可以向本人提出書面通知,并且直接對其起訴,但范圍只限于本人在接到通知后應對代理人所承擔的責任。〔53〕 第三人的選擇權在美國很多州受到了攻擊,在這些州第三人獲得了大翻盤,他們爭取到了針對本人的額外的權利,而不是原來的選擇性權利。他們成功地說服了法院,第三人只享有選擇本人和代理人其中之一的權利是不公平的,因為在關鍵性的代理人破產的情況下,往往會僅僅因為第三人犯了相信代理人有足夠的資產償債的錯誤,便使本人從交易中獲取利益而不必履行自己的義務。〔54〕摒棄第三人選擇規則(the election rule or election of remedied rule)已經成為一種趨勢,時下在美國的多數州,法院要求本人和代理人對第三人承擔連帶責任
第三人主張權利,是指在已經開始的訴訟中,對他人之間的訴訟標的,具有全部的或部分的獨立請求權,或者雖然不具有獨立請求權,但案件的處理結果與其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的人。


